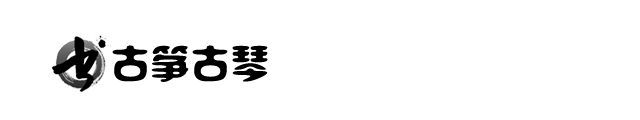阮武昌年轻时的阮武昌阮武昌的手模镌刻于齐齐哈尔市和平广场抗战纪念墙上从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开始,到1945年年底,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一直忙于接受驻华中地区日伪军的投降。然而,说得准确一点,所有这些地方,都不是通过受降仪式、不费一枪一弹“接受”来的。相反,大多是通过激烈战斗,在打得日伪军无路可走以后,才迫不得已向我军投降的。
这种情况,在古今中外的受降史上恐怕也是少见的。——阮武昌人物小传阮武昌,1929年生于江苏如皋,1943年入党。
1944年12月参加新四军。先在苏中军区如西县独立团,后改编为新四军一师一团,任政治干事;1946年5月至1952年间,先后在三野四纵十师所属单位及第九兵团教导团任干事、支部书记、副政治指导员、政治指导员;1952年7月至1953年12月,参加抗美援朝,任志愿军炮兵四零五团宣传股长;1970年6月,调至上海警备区工作,并于1983年起任上海警备区副政委。
1993年离休,离休后任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会长。总算熬到头了是啊!整整八年啦!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中国人民流淌了多少血泪?经受了多少苦难?这下好啦,天终于亮了。1945年8月10日左右,我正在一个区的游击队里工作。
傍晚,团部通讯员骑自行车送来了一封急信。当时通讯员一面擦着脸上的汗水,一面笑着对我和区队的队长、指导员说:“好消息,快看!快看!”听他这么一说,队长赶紧把信拆开,一看,真的是天大的好消息——日本马上就要投降了!毛主席、朱总司令还命令我们立即举行反攻,去收缴敌人的武装。看完信,我们三个人差点要跳起来,都说应该把这个好消息尽快告诉大家。于是立即集合部队,向大家传达。
信一念完,一下子像炸了锅似的一片欢腾。大家叫呀,跳呀,说呀,笑呀,有的挥动双拳,有的拼命鼓掌,有的举起双手,高呼“我们胜利啦!我们胜利啦!”不少战士还拿出随身携带的搪瓷碗,代替锣鼓叮叮当当地敲了起来。随后,大家纷纷涌向我和队长、指导员,要求赶快开赴前线,去执行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出的接受日伪军投降的命令。
很快,消息像风一样传遍全村。不大一会儿,村上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成群结队来到部队集合的场地,和指战员们一起欢庆胜利。场地上三五成群,欢声笑语。
有些人高兴地拉住战士跳起了秧歌舞,还有些人激动地爬到草垛上放开嗓子喊。一位老奶奶一边用手擦拭着脸上的泪水,一边不停地自言自语:“总算熬到头了!总算熬到头了!”还有不少男青年当场要求参加新四军,去和日军做最后的一战……是啊!整整八年啦!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中国人民流淌了多少血泪?经受了多少苦难?这下好啦,天终于亮了。
苦难的日子终于熬到头了,我们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而侵略者也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报应。不想回家的孩子一个身材矮小、穿着一身又肥又长的破军装的伪军主动站到了我的面前。
遵照毛主席、朱总司令下达的“解放区抗日军队,统应举行积极进攻,迫使日伪军无条件投降。如遇抗拒,应坚决消灭之”的命令,部队立即向如、黄线挺进,对驻守那里的日伪军采取行动。8月14日下午,我们首先包围了该县中段的分界镇。
这里驻着伪军一个营,总共三百多人,由一个副团长率领。一开始,这帮人很狂妄,还想采取拖延战术,说是让他们再考虑考虑,明天再说。
看来不施加点压力不行。于是团长命令把两门土炮架起来,瞄准炮楼打了三发炮弹。由于距离很近,三发炮弹倒是发发命中。
可是因为终究是土造的,材料不过关,因此三发当中只有两发爆炸,而且威力似乎不是很大。不过尽管如此,敌人还是害怕了,马上从炮楼的枪眼里伸出了一面白旗,表示愿意向我们投降。后来经过谈判,午饭之后敌人终于放下武器,三百多人在副团长率领下,整队离开据点,到指定地点集中。
下午,我和另外一个同志负责去处理这批投降的伪军。本着“凡是愿意留下的交给司令部分配到各连,凡是不愿留的,发给一定的遣返费让他们自己回家”的原则,我俩分别和伪军逐个谈话征求意见。当我刚谈完一个还没有来得及喊下一个的时候,一个身材矮小、穿着一身又肥又长的破军装的伪军主动站到了我的面前。
一看,是个孩子,大约十三四岁的样子。脸上还有几颗浅浅的麻子。“叫什么名字?”我问道。“郭家宝。
”他低着头漫不经心地回答。“在那边干什么的?”“号兵。
”“希望回家是吧!”我想这孩子一定很想回家。“不!”回答得斩钉截铁,这倒引起了我的注意。
“为什么?”我又问。“我没有家。”这次他说得又慢又轻。
“父母亲呢?”“家里穷,生病之后没钱治,早就死了。”几句话,说得我心里酸酸的。“那你怎么办呢?”“留下来!”“新四军的生活可是很苦啊!”“我不怕!”他很倔强。
看着他这个样子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于是同意他留下来。他一听让他留下,挺认真地向我鞠了个躬,然后赶紧站到留下来的那一边。巧的是,半年多以后,我又见到了这个孩子,并且还成了他的直接领导。
本文来源:JN江南体育-www.epwuti.com